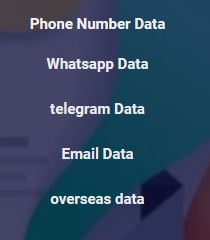也许批评者错了,但我不这么认为。(我认为没有理由假装对这些斗争保持高高在上的公正,认为扮演历史相对主义者是老练的做法,认为我作为政治理论家的工作只是描述发生的事情。)但也许。也许让国家或国家元首对他们的行为负法律责任不是一个好主意。也许让国际组织甚至假装行使权力不是一个好主意。也许将权力划分给联邦政府和州(省、州……)政府不是一个好主意。也许将宪法限制固定下来并执行不是一个好主意。在所有这些情况下,我认为,我们应该进行零售,而不是批发。也就是说,我们不应该假装通过诉诸主权来解决问题,而应该探索正反两方面的理由。
例如,如果外交官真的能够逃脱谋杀罪,这说得通——当然,1961 年和 1963 年的《维也纳公约》将外交豁免权扩大到一支小型军队,远远超出了大使的范围——那不可能是因为主权权威的本质。这一定是因为将自己的使者托付给外国法 智利 WhatsApp 号码数据 律,让他们成为厄运的人质,这很危险;然后你还必须反过来向他们的使者提供针锋相对的回报。同样,,所有关于主权的讨论(“最重要的是,”下议院领袖坚持说,“这是一场恢复我们国家主权的运动”)提供了一个可悲的例子,说明坚持一个糟糕的理论会带来多么严重的后果。我错了吗?当然。 (一直如此。)但这并不是因为英国已经损害了其主权并需要收回它。
我可以(也确实)通过提出一个两难的局面来加强论证。现在,诉诸主权要么有害,要么毫无意义。当人们仍然明确或含蓄地坚持政治权力应该是无限的、不可分割的和不负责任的理论(甚至其中任何一种理论)时,诉诸主权就是有害的。无论几个世纪前这种想法有多好,现在它们都是可怕的。我们已经了解到太多关于“能够震慑所有人的权力”会造成多大的破坏。
当人们否认经典概念的所有三个标准但继续谈论主权时,诉诸主权就是毫无意义的。(想象一下说“这是个单身汉,但不是未婚男性。”)至少,他们有责任告诉我们他们的意思。许多作家,至少有一位代表参加了这次研讨会,提出了重构主权概念的方法。我认为,最好把它扔掉。国家、权威和管辖权的概念已经触手可及。它们并非毫无困难。但它们并不体现主权的怪异极端主义承诺,而且我们无需做任何进一步的工作,因为没有它们我们就无法做到。
- Board index
- All times are UTC
- Delete cookies
- Contact us